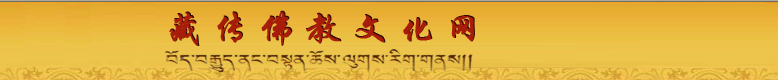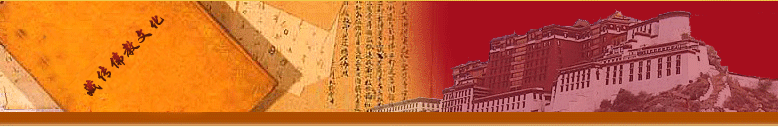|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比尔·波特来到陕西终南山,寻找中国的隐逸者。比尔的寻找结果形成了一本书———《空谷幽兰》。这本描写当代中国隐逸者的书去年被翻译再版,在不事声张中耐人寻味地获得了读者的青睐。而转过年来,“林妹妹”出家的新闻覆盖了媒体。这两个表面上没有联系的事件其实有一个共同指向,那就是当代部分中国人的精神处境。
近年来,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人士,在人生得意之际突然落下风帆,离弃人群,选择隐逸。在一个越来越能包容的社会里,这样的选择固属个体意志的展现,但其孤绝的背影还是不能不让我们生发探询的兴趣。
A 出身名校的佛门弟子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触了佛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这样的修行生活显庆法师已经过了一年有余。在成为法师之前,他的名字叫邓文庆,拥有令人羡慕的北京大学硕士头衔。法庆的出家过程简洁而迅速,事先并未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亲友。“毕业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直到看到报道才知道。”一名哲学系的同学说。
法庆的事之所以被报道出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耕读社”和“国学社”的80名学生来到凤凰岭龙泉寺体验生活,他给同学们讲课,被认了出来———当年的邓文庆,曾是“耕读社”的首任社长。
“耕读社”是北大一个以“诵读传统经典、学习传统文化”为宗旨,理念和实践并重的学生社团,成立于2002年。主要的活动包括经典诵读、读书研讨,也做一些有机农业推广、社区教育等实践活动。据参加过“耕读社”成立早期活动的一名2001级本科生回忆,邓文庆看上去很沉稳,“当时就觉得他的话有些佛法的味道。”
北大清华都有出家人
邓文庆并不是北大哲学系****位选择出家修行的学生。现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师就是北大哲学系87级学生,他于毕业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禅寺从净慧老法师剃度出家,现在已经是佛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忆起接触佛教的缘起,明海法师说,**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师的传记,忽然发现人生原来还有那样一些值得追求的东西。后来,一位同学又送给他一盘台湾的星云大师讲法的卡带。就是这盘卡带,让明海产生了去寻找高僧大德学法的念头。通过师长介绍,他结识了时任广济寺方丈的净慧法师。
但是,真正决心出家却并不容易。明海**初的计划是先工作、结婚生子、给父母养老。“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40岁出家,差不多吧。”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初的打算。
毕业之后,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上完课就在办公室打坐。冬天的时候,他跟净慧师父去柏林寺“打禅七”,却发现原来要修的还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还是半个废墟的柏林寺,他看到师父们尽管条件相当艰苦,“精神面貌却这么好”。出家的念头一下子萌发出来,而且日益茁壮。经过半年多的考虑,他终于下了决心。
和他的学弟邓文庆一样,明海法师的出家也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但是,很快父母也“被动接受了”,他们后来也都成了佛教徒。
在柏林禅寺,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生明影法师。此外,至少还有明恭、明一、明勇三位法师都是上个世纪毕业于****大学的学生。
在江西,江西佛学院常务副院长衍真法师是上世纪80年代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
而据龙泉寺一位法师透露,在龙泉寺,“现在清华的研究生比北大 的多!”
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这些“天之骄子”们选择出家,大多不是因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触了佛教理论并为之吸引后作出的一种人生选择。
出家是否逃避社会责任
选择出家修行这样一种人生的,并不止于年轻的学生。也有许多人,在学佛多年以后选择了出家。
曾经看过早期《今日说法》的观众,或许会记得经常在节目中担任嘉宾的两位气质优雅的女法学家,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学的王小能。而后者已经于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现在五台山隐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王小能出家前已经评上教授职称,是票据法领域的专家,工作顺利,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也有美满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学素食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哲学系毕业生王文利对记者介绍,王小能老师学佛多年,同事学生都知道。“她早就戒了荤酒,自称在家是‘一锅两制’。她很早就计划要出家,但是她师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劝她等孩子大一点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预期。”
同样在五台山,还隐居着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誉为“****神童”的宁铂。这位中国少年班****人,曾是上世纪80年代无数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学毕业之后人生却一直不顺,选择出家之前他只是中国科大的一名普通教员。
直到2003年出家,宁铂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许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对宁铂而言,这是他****次自己选择人生———虽然也曾被校方劝回一次。现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气,但却不再愿意谈起与“宁铂”相关的往事。或许,那个“宁铂”并不是他的真我,现在才是。这正如陈晓旭出家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林妹妹终得其所!”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近的“林妹妹出家”。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B 终南山的隐士们
“师父在的时候,有任何财物都及时施舍出去,自己只有一件袈裟。我现在有些个人的东西还舍不得送出去。”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何有,有纪有堂”。《诗经·国风》所说的终南山,又称南山,在上古时期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用来指今天的秦岭,也可以延伸到乔戈里峰。而现在所说的终南山,指的是在西安南面40公里左右的系列山峦。
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临近长安,而又深邃幽静,终南山便是高人隐士们隐居的****场所。“终南捷径”这个成语便出自此处。同时,这里还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中国佛教的第二策源地,从长安自山脚,分布着众多名观古刹。
而到了现代,终南山又因山中的众多隐居潜修者而知名。近代四大高僧之二印光、虚云都曾在此隐居。著名佛教居士高鹤年在《名山游访记》中称赞说:“名山修道,终南为冠。”
不再安静的楼观台
3月中旬,记者来到了西安西南70公里处的楼观台,这里是传说中老子传授道德经的地方。楼观台的住持是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但是他现在不在观里,而在西安的八仙宫忙着筹备道教论坛。记者见到他时,任道长正和许多人谈话,据说午饭都没顾上吃。
楼观台也是一样的繁忙,因为次日是老子诞辰,这里正在举行庙会。山脚的街上和公园里摆满了小摊,观门口则有许多乞讨者。
记者沿山路一直登到山顶的炼丹炉,据说这里是老子炼丹得道的地方。根据《空谷幽兰》一书记载,十多年前这里的主事是一位姓苏的女道长。现在,小小的祠堂里站着的是一位男道长。记者问起苏道长,他激动地说“走了!走了!”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屋里的烟气实在太重,他眼里流着泪水。
而祠堂边卖香火的谭姓村民告诉记者,苏道长多年前便到山下休养,已经去世,现在这位道长是山下派来接替她的。记者问起山里是否还有独自居住的道长,他指着远处的一间茅屋说,以前那间屋子里有人住,现在都搬到山下了。
确实,这里太热闹了,不像是能找到隐士的地方。
终南山**美的茅蓬
南五台在西安以南35公里处,因为有五座山峰而得名,当地村民索性称之为“五台山”。在南五台的山谷中居住着许多佛教出家人,他们或独自、或三五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甚至山洞中,他们的住所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茅蓬”。
据村民介绍,现在在山中住的**久的是“净土茅蓬”里的乘波师太,她至少已经住了28年。而乘波的两位师父———慧因师太和慧圆师太,在这里住的时间更长。据乘波师太介绍,这两位师太都是解放前的大家闺秀,受过高等教育,三四十年代便出家了。两位师太都是东北人,1955年在北京开会时结识,一起寻找地方隐修。来到南五台后一看,“就是这儿了!”两位师太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圆寂。而1975年,家在西安的乘波跟朋友一起来看望慧因师太,像她的师父们20年前一样,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
谈话的时候,乘波师太坐在院里的一颗苹果树下。院内还有几棵桃树,粉红的桃花开得正艳。远处的山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朦胧的月光照在桃花和屋后的清泉上,非常诗意。很多来过终南山的人都称赞这里是“**美的茅蓬”。“净土茅蓬”现在住着三位尼师,乘波师姐妹和她的一个徒弟。房屋就是佛堂、卧室和厨房。记者看到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佛堂内更是一尘不染,各种器具和书籍摆放整齐。厨房墙上还挂着一口钟———据山下的法师介绍,她们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每天都按时敲钟上堂,一丝
不苟地遵从寺庙的规矩。
“我比我师父差远了。师父每天除了干活都在做功课,除了念佛,每天还念七遍法华经。我的精进差多了。”说起这话,乘波师父微微低下了头。
她又说,“师父在的时候,有任何财物都及时施舍出去,自己只有一件袈裟。我现在有些个人的东西还舍不得送出去。”
(均据《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17期殷俊/文)
C 隐逸文化的根脉
中国自古多有隐逸之士,他们成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从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是隐逸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孔子虽一生周游列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理论上他也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自己就身先士卒做了避世全身隐士;佛家则是**纯粹的弃绝红尘之隐。
随着文化的发展,隐逸渐成一种自我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其中也包含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清高的人格理想、淡泊宁静的生存方式和典雅的文化品位。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为此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现代工商业社会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加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原因,使传统的隐士近乎绝迹,“隐”起来越来越难了。然而,隐逸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断绝。
自唐宋禅风大畅以来,亦官亦隐、亦僧亦俗,一度成为一种时尚。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人们都可以一方面着眼现实,属意名利,一方面心向山林,志归禅道,二者兼顾。“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等理论不仅使佛渐渐向现实世界靠拢,更为归隐修行大开方便之门。宗教也在不断调节,改变形式和理念,适应现代社会。
丰子恺曾经总结,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学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着这个楼梯一层层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尤其佛教,度一切众生,因此,还有很多人更愿意到佛的屋檐下避雨。
(柴爱新/文)
编辑:alaya 来源:《文摘周报》07.5.1-08社会版
版权属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和《藏传佛教文化网》所有,转载、复制请注明出处。
|